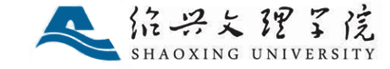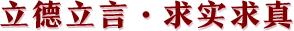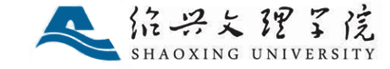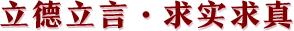到词语的产地去——人文游学行日记整理之三
一篇文章好不好、影响大不大,我的标准其实很简单,看它出产了多少个词语,而不是看它使用了多少个成语,满篇成语的,那是成语接龙。
《论语》影响大,几乎每章每句都有资格成为词语,如“不亦乐乎、朽木不可雕、造次、而立、不惑、耳顺之年、闻过则喜、见贤思齐”等。华文中的词语多产自古代诗文,现代诗文中脍炙人口的词语不多,比如海子的“春暖花开”,或者像食指的“相信未来”,还有郑愁予的“美丽的错误”等等。伟大的文章诗歌,是来这个世界给万事万物命名的。
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底蕴,也有一个语言学标准,就是看这个地方出产了多少个词,该地是不是汉语中词语的高产区。
很多地方,因为一篇文章名扬天下,比如绍兴兰亭,全凭《兰亭集序》,该文不仅是“天下第一行书”,更是一篇思考生死的名文,325个字,从“山、水、天、风”的“信可乐也”,到“修短随化”的“岂不痛哉”,再到“一死生齐彭殇”之“悲夫”,情感波澜起伏,道尽魏晋文士的生死之痛,更产出了如“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、清流激湍、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、映带左右、畅叙幽情、曲水流觞、放浪形骸、修短随化”等典雅成语。有了这篇文章,产出这些词语,兰亭——词语的高产区,便成为一个很多文人墨客或者有文化的酒徒神往之地。
2015年和2016年两个暑期,我和几位老师,带着一群学生,人文游学中原行,第一年到山东河南,沿着孔子周游列国的足迹;第二年到陕西山西,走的是秦王东扩一统天下的老路。中原那地界,是词语高产区,最著名的当然是“中国”,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“中、国”这两个汉字连用,在当地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,何尊真品不在馆藏之中,复制品前依旧人头攒动,大家都在找铭文中那句“余宅兹中国,自兹牧民”,天花板上投影出“中国”二字,如日月当空。还有“华夏”,据说这“华”指的是华山,“夏”指的是黄河北岸的运城,那地方是夏朝的地盘。
当然,更深刻的词语是“秦晋之好”,每次看到新婚时大门喜联横批是“秦晋之好”,就肃然起敬,秦晋两个国家大致以黄河为界,但是更多时候是争斗不休,扯不清,春秋战国数百年,秦晋和睦相处的时间据说也就几年而已,其他时间,或貌合神离,或干戈相对,“秦晋之好”来做新婚横批,真是一语道破天机。简直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:一孙子问大爷,为什么结婚的时候都要选个好日子?大爷沉吟片刻,大喝一声:“孙子,结婚后,就没你的好日子过了。”
游学第一站是陕西宝鸡,“宝鸡”这个名太现代了,像我们这样食古不化的,更亲近的地名是“陈仓”“大散关”,又是一些著名的成语如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”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等让我们熟稔这些词语,这些词语带着血色散发着青铜器般的苍凉之气,站在秦岭的那个关隘口等着我们。如果把这些熟语改为“暗渡宝鸡”“铁马秋风大宝鸡”就有些无厘头了。
有些词语,一定要到它的产地去看看,才知道这个词语有多丰富。比如五丈原,应该写作五丈塬吧,“塬”这个词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很陌生,但是对陕西人来说是个常用词汇,大巴司机张师傅就不停地使用这个词,张师傅是宝鸡人,他说“塬啊,就是指高高的一块平顶。”那么“五丈原”究竟是“塬高五丈”,还是“塬上风高五丈”?“风高五丈”,风怎么有高度呢?哦,是龙卷风。
岐山有姜子牙钓台,中国人都熟知一个成语“愿者上钩”,可是最近看俞志慧老师的一篇文章,讨论真实性和正确性的问题,说诗经中就有姜尚先生“维师尚父,时维鹰扬”,“鹰扬”也是一个很古雅的词,照字面解释,是不是“如鹰般飞扬”?可见姜尚并不是八十多岁了还在搞行为艺术,应聘找工作,这位老兄应该在青壮年时期就已经驰骋沙场,扬名立万了。
我们的世界是词语建构起来的,我们阅读了什么样的文本,和什么样的人交谈,听过哪些词语,我们对外面的自然山川就有了一种新的视角。据说,没看过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人,很难领略江南山水的美。可见艺术在建构我们的审美情趣,词语符号则搭起文化偏见的阁楼。
很多成语都是有产地标识的,这些词语会让我们对那个产地产生一些不着边际的遐想(瞎想),我们眼中的山川之美,一半出自自然造化,另一半源自文史篇章、词语诱惑。
“假虞伐虢”这样的词语地理标记很明显,“唇亡齿寒、辅车相依”这样的现场感就不太清晰了,不过超越了具体的地理限制,“唇亡齿寒”倒是更为通行,这些成语来自《左传·僖公》: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谏曰:“虢,虞之表也。虢亡,虞必从之。晋不可启,寇不可玩。一之谓甚,其可再乎?谚所谓‘辅车相依,唇亡齿寒’者,其虞、虢之谓也。
《左传》也是伟大的著作,其中很多典故,千百年来依旧作为成训,约束古今,是故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。看来“唇亡齿寒、辅车相依”在遥远的春秋,就已经是当时的成语了。
更有成语“泾渭分明,泾以渭浊、浊者自浊,清者自清”云云。从宝鸡到咸阳的路上,我问俞志慧老师:“泾水在什么地方汇入渭水?”他回答说大约在咸阳机场附近吧。到底是泾水清还是渭水清,古来争论不少,已成疑案。这时我们也看到成语的可怕,大部分人都相信成语中的说法,泾水是清的,渭水是浊的。考证再多,也很难改变一个成语的流行所带来的偏见。
让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思想词汇化,才能真正入脑入心,尧舜禹成为三皇五帝,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,首先要让这些人的名字成为高频使用的词语,在不同地域的口说笔抄之中。“禹迹”是古代华夏文明地理区域的代名词,所谓“茫茫禹迹,画为九州”,宋代的全国地图,还称为“禹迹图”。
秦晋之民用信天游唱着大禹出禹门、石门、龙门的故事,齐鲁之士说着禹县旧闻,湘楚之人坐在禹庙前说着衡山上的岣嵝碑上的刻石,吴越之众说着大禹葬于会稽禹穴,当这些人偶然相遇,用各自的方言艰难地交流的时候,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天下一家,大家都是大禹的后人,感叹道:“微禹,吾其鱼乎”,或许一个文化共同体——华夏民族就这样逐渐形成了。词语组合成八卦故事,八卦构建文化观念,文化观念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形态。
爬完华山,下山就到了潼关。“潼关”在我脑中成为一个意象,是因为张养浩先生那一首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:
峰峦如聚,波涛如怒,山河表里潼关路。伤心秦汉经行处,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百姓苦,亡百姓苦。
“河山”、“山河”,这样的词语组合很悲壮,“还我河山”一词更是藏着南宋君臣揆心的微妙,黄河、华山本是华夏祖地,岳飞、陆游等却只能在南方遥望,身在沧州心老天山,而赵构等人则偏安一隅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悲壮之词,更有诱惑力,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先生《地可以怨否》中说:
对游者而言,不在收揽美景,而在巡游古迹。凭吊怀古,又以哀怨为情景最高。游那些新漆的庙宇,乍刻的石阙,怎比得上吊汨罗江听潇湘雨寻赤壁戟?
原来不仅诗可以兴观群怨,地也可以,只是兴观群怨都要靠词语来完成。绍兴报仇雪耻之乡,盛产词语,很适合兴观群怨,其中“卧薪尝胆”是兴,“十年生聚”是群;“应接不暇”、“云蒸霞蔚”、“雪夜访戴”是观;“沈园柳老”“王师北定”等便是怨了。
2016年游学最后一站到了河南的三门峡,函谷关在那。
除了盛产恶战,函谷关还盛产词语,据说此地关令尹喜见紫气东来,知李耳老先生骑青牛出关,便请老先生著书讲学,老先生拗不过当官的,只好强为之言,留下了句句皆成语的《道德经》,处处抖机灵,字字有机锋,“绝圣弃智、绝仁弃义、见素抱朴”等成语在汉语儒家正宗中不是主流,但也因其另类,装深沉的家伙都喜欢。
当然,函谷关还产出了“鸡鸣狗盗”,是个贬义词,不过,作为原产地,函谷关内的电子仿真鸡鸣狗盗之声,讲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,身有小技,方得通达。如果只是掌握了屠龙刀法的道德标兵,到此关前,也只能长叹一声“天下无龙可屠哉!”在这个词语面前,那些以道德高尚、明辨是非自居的大人君子,只能自叹小时候口技功夫不好,翻墙之功不到家。
词语浩瀚,我们所能掌控的,只是沧海一粟,凑巧知道这个成语,倘若没去过这个产地,毕竟和词语隔了一层。只有当这些诗文名篇中的词语变成有声有色有气息的场景时,这些词语才会真正融入我们的心胸,只等某一天我们看到听到这些词语,当时登临的天气、伙伴、声色犬马都会马上激活,为那个词语添油加醋,酸甜苦辣千般滋味,一发滚上心头,就有了现场感,这时我们就可以言说一次独特的体验,这是别人无法复制的。
就像以前只在书中见过鲁迅先生的照片,胡乱翻先生的文章,后来落户绍兴,才知道S城的各种风土习俗,从百草园跟着人群走,走到三味书屋,虽已不见先生家后院的那两棵突兀的枣树,但是对先生眼中笔下的越地三乌(乌毡帽、乌篷船、乌干菜)气质、酒楼风波,就有了更具色香味的体认。
链接地址:http://epaper.sxnews.cn/sxrb/html/2017-03/20/content_7_1.htm